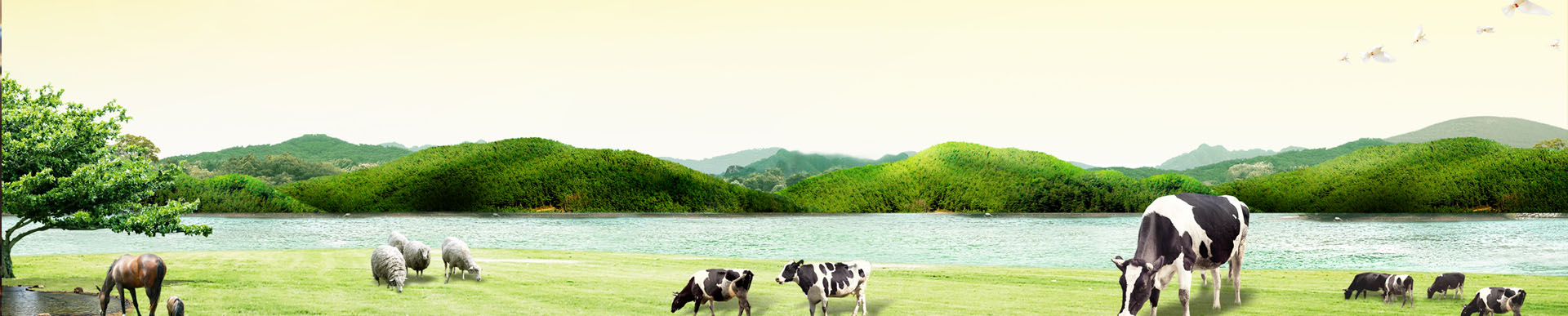138項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四川有8項 讓農耕文明的“活化石”活起來

7月中旬在浙江省青田縣舉行的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大會,讓更多人認識了“農業文化遺產”——
流水潺潺的稻田里,水稻為魚提供生活環境和食物,魚為水稻松土施肥,魚稻相依、和諧共生……稻魚共生的畫面,讓很多來自不同國家和國際組織的代表印象深刻。1300多年前,青田的先民,智慧地發展出“以魚肥田、以稻養魚、魚稻雙收”的稻魚共生系統,也在2005年被認定為世界首批、中國首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
農業文化遺產是中華農耕文明的“活化石”。作為農業大省,四川農業文化遺產的發掘、保護和利用是一個什么樣的情況?
現狀
8項系統入選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名錄
擁有深厚的農耕文化底蘊,卻沒有形成文化遺產的影響力
農業農村部迄今共認定了138項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其中四川有8項,成都市郫都區就有一項。
8月上旬,郫都區郫筒街道、德源鎮、友愛鎮等地即將迎來大豐收。水田里稻谷成片,旱地里生姜長勢喜人。在這里,水旱輪作、立體種植、稻田養魚、林盤綜合利用等生產模式,實現了資源利用最大化和精耕細作。
郫都區作為都江堰灌區首灌區,這里有沿襲千年的川西傳統農耕文明,滋養了全域8700余個人居林盤,保留并傳承了獨具川西平原特色的林盤農耕文化系統。
2020年1月,“郫都林盤農耕文化系統”入選第五批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名錄。這是一個以傳統人居林盤為核心,由農田、林地、房舍和自流灌溉渠系組成的復合生產生活系統,遺產地覆蓋郫都區12個涉農街道(鎮),總面積278.1平方公里。
“四川是農業大省,農耕文化歷史悠久、源遠流長。”農業農村廳相關負責人介紹,近年來,我省大力挖掘、申報農業文化遺產。收入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名錄的,除了郫都林盤農耕文化系統,還有江油辛夷花傳統栽培體系、蒼溪雪梨栽培系統、美姑苦蕎栽培系統、名山蒙頂山茶文化系統、鹽亭嫘祖蠶桑生產系統、宜賓竹文化系統、石渠扎溪卡游牧系統。
2020至2021年,我省累計投入2630萬元,分兩批次重點支持成都市郫都區、自貢市沿灘區、崇州市等27個縣(市、區)開展農村生產生活遺產保護傳承工作,已收錄農村生產生活遺產310個。此外,近年來我省連續5年開展農村手工藝大師評選活動,評選出農村手工藝大師207人。
“雖然資源豐富、挖掘潛力巨大,但瓶頸也比較突出。”農業農村廳相關負責人說,全省農業文化遺產挖掘、保護和利用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一方面,不少地方雖然擁有深厚的農耕文化底蘊,但缺少農業文化故事挖掘,僅在很小范圍內傳播,沒有形成文化遺產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已經挖掘打造出來的不少農業文化遺產資源,比如部分地方建設的農業博物館、村史館、農具展廳等,僅作為鄉村旅游的一個看點,未得到充分綜合利用,變現能力不足。
此外,不少文化人士收藏的農耕文化器具,大多存放在保管室里,處于“養在深閨人未識”狀態。
探索
缺乏真金白銀支持,制約農業文化遺產“活”過來
保護和利用農耕文化,與文旅發展融合提升附加值
為何出現上述瓶頸?在農業農村廳相關負責人看來,首要原因是整體上對農耕文化保護和利用認識不足、重視不夠。目前,我省尚未從整體規劃、傳承舉措等方面作出制度性安排,導致總體投入不足。
“每年投入支持開展農村生產生活遺產保護傳承工作的經費不穩定,而且平攤到各縣也就幾十萬元,可能建個農耕博物館都不夠。”該負責人坦言,對于入選全省農村生產生活遺產名錄的,目前暫時沒有真金白銀和項目支持。
人才也是短板。相關專業人才培養跟不上,有的傳承人和受眾群體出現斷層。“這也許是我的收官之作。”指著宜賓市江安縣郊區一棟竹藝工坊,白發蒼蒼的何華一這樣告訴記者。他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江安竹簧的代表性傳承人,做竹根雕需要美術、書法、雕刻等多種技藝,而提升這些技藝需要成本。“熱衷于竹根雕手藝又甘坐冷板凳的年輕人實在難找。”
“農業文化遺產具有超越時間的重要價值和強大生命力,是培育特色品牌農業的重要依托和先天優勢,又是發展鄉村旅游極具魅力的看點。”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郭曉鳴說。制約農業文化遺產挖掘保護利用的另一個短板,是缺乏與相關產業有機融合的激勵政策。“農文旅融合,是提升綜合附加值的有效路徑之一。”農業農村廳相關負責人表示,江油辛夷花傳統栽培體系、蒼溪雪梨栽培系統、名山蒙頂山茶文化系統等,都是將農業文化遺產挖掘與當地農特產品生產銷售、生態旅游業緊密結合的典范,但部分地區沒有把保護和利用農耕文化擺上促進文化旅游發展的議事日程,缺少深度融合、統籌安排和保護措施。
“我們這里草原遼闊壯美,游牧文化獨具特色,但高寒缺氧,離大城市較遠,交通不便,發展旅游業挑戰不小。”石渠縣農牧農村和科技局工作人員坦言,當地農業文化遺產目前仍以挖掘、宣傳和保護為主。
如何保護好農業文化遺產、更好地發揮其價值?在農業農村部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閔慶文看來,農業文化遺產肩負著經濟發展、生態保護、文化傳承多重任務,如果盲目開發,勢必造成破壞;如果過分強調原汁原味的“冷凍式保存”,而忽視區域發展,則難以調動當地居民文化遺產保護的積極性,也難以實現保護的目的。因此,需要探索保護與管理的新思路。
對策
摸清遺產資源底數,建立檔案名錄庫
培養“新農人”,吸引有情懷的人回歸農業
“既要高產量,也要高顏值。”這幾天,攀枝花市米易縣新山傈僳族鄉新山村第一書記邱榮新,多次和村組干部一起下梯田、問專家,力爭依托梯田資源打造農業文化遺產樣板。
新山村梯田,由居住在這里的傈僳族居民世代耕作,已有上百年歷史。“最近有部分村民提議田改土,種芋頭、筍尖,以提高產值,這個問題要慎重。”邱榮新說,保護好梯田資源是保護和利用農業文化遺產的基礎。
為全面摸清我省梯田的存量、保護利用的主要方式方法、存在的問題和困難,農業農村廳日前組織人員,到米易縣、洪雅縣、天全縣等地開展梯田保護與發展專項調研。
“摸清底數,是推動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的前提。”農業農村廳相關負責人說,下一步,計劃通過開展類似調研,建立農耕文化遺產檔案名錄庫,全面系統記錄各類農業文化遺產,作為農耕文化保護利用的原始依據。
保護利用農業文化遺產,針對其長期性、復雜性特點,專家建議,對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鮮明、保護意義大、留存價值高的農耕文化要重點保護傳承利用,建設農耕文化展示區、民風民俗特色小區等,打造一批具有特色的農耕文化品牌,發揮引領和示范作用。
“城鎮化發展、農村勞動力轉移是許多農業文化遺產地面臨的現實問題。”對此,閔慶文建議,引入現代農業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理念,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率與效益。同時注重培養“新農人”,吸引有情懷的人回歸農業,浙江青田和湖州、內蒙古敖漢等地已有成功案例。(記者?王代強)
延伸閱讀
為什么要讓農耕文明的“活化石”活起來
“國有史,邑有志”。農業文化遺產的存在,何嘗不是對中華農耕文明閃光點的最佳傳記、鮮活載體——它是對人與環境共處碰撞無數種可能性的探索,更是千百年來鄉愁的傳承。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與鄉村可持續發展研究”首席專家、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孫慶忠曾說,保護農業文化遺產表面上是保存傳統農業的智慧,保留和城市文化相對應的鄉土文明,其更長遠的意義,則在于留住現在與過往生活之間的聯系,留住那些與農業生產和生活一脈相承的文化記憶。這不僅是弘揚農耕文化的精神基礎,也是社會再生產的情感力量。
保護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不是讓農業現代化倒退、回歸原始農事生產,而是不忘根本、借古思今,再次激發我們對于“歸雁有巢,鄉愁有根”的眷戀和思考。只有將保護農業文化遺產的意識筑牢,才能避免我們與后代在追逐現代化的過程中,喪失對生產和生活經驗的傳承能力,避免失去民族文化特質,獲得基于歷史認同的安頓心靈之所。(據《四川農村日報》)